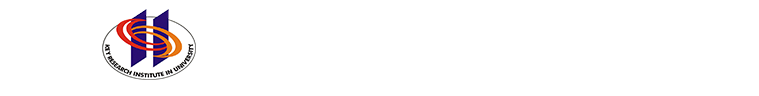“国际世界史研究前沿与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 高层论坛综述 2012年7月6日-8日,“国际世界史研究前沿与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高层论坛在湖南张家界召开。此次会议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与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由湖南吉首大学协办。来自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以及《世界历史》、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单位的25位专家与会。会议主题有二:一是国际世界史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趋势以及热点问题;二是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后的学科建设问题。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围绕上述两个议题进行了紧张而热烈的讨论。 在第一个主题的讨论中,与会学者首先阐述了各自研究领域的国外内研究状况。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张顺洪研究员就英帝国史研究中的殖民地公职机构的研究状况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在1997年以前,英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不多,主要代表人物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柯克夫人。该问题的研究高潮出现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英国学界认为,香港回归是殖民地公职机构的终结,因此学术界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相关论文集。但是,英国学者并没有就这一问题撰写出学术专著。北京大学高岱教授也讨论了当前英国史和英帝国史的研究状况。他首先补充了张顺洪研究员关于英帝国史研究的一些信息。英国史学界目前出版了一套20卷本的英帝国史,这套著作的特点是针对以前对帝国与殖民地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从宏观角度做了很多理论探索。另外,高岱教授还指出,英国学术界现在尤为关注英国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前对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关系研究较多,现在开始关注英格兰与苏格兰、威尔士之间的关系。最后,他还呼吁加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因为一战对欧洲影响很大,对英国尤其如此。比如,一战极大地促进了英国民主化进程,扩大了英国男性和女性的选举权。 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关注的是美国早期外交史研究。他认为,美国早期形成的外交理念对后世的美国外交影响很大,对理解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和当代美国外交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对这一理念研究得透彻,我们就能把握美国外交发展的脉络。王晓德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美国早期外交的资料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很多早期史的资料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有了丰富的资料,中国学者才有了深入研究的基础,甚至能够纠正美国学界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偏颇。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徐再荣研究员考察了美国灾害史的发展轨迹。他认为,早期的历史学并不关注灾害,灾害也不关注历史,形成了所谓的“灾害遗忘历史,历史学遗忘灾害”的局面。1970年代以后,以唐纳德·伍斯特的《尘暴》为标志的历史灾害学兴起,前述局面才被打破。徐再荣研究员指出,70年代末兴起的灾害史主流还是环境史视野中的灾害史,强调灾害发生的人为原因,强调灾难中人与自然的互动,揭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灾难性影响。80年代后,灾害史开始了社会史转向。社会史视野下的灾害史强调灾害与社会的互动,灾害发生后人与社会的互动。在社会史学家看来,灾害史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灾害何时发生、何时结束,如何处置等,因不同社会条件、不同权力关系而异。还有学者分析了灾害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一种破坏性关系,而且是形成一种共生关系。灾害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内在因素,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更新,即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南开大学陈志强教授则讨论了国内外拜占庭史研究的进展。2012年6月份,南开大学首次在国内召开了拜占庭研究圆桌会议,有20多位学者参加,已经初见规模。在国际学界,拜占庭研究的规模都很大,仅仅美国就有300多位专职从事拜占庭研究的学者。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学者从事拜占庭研究,是大国心态的反映。美国力图在各个研究领域都要有自己的声音,而且要做到最好。接着,陈志强教授以牛津拜占庭史为例讲述了国外拜占庭研究的新进展。在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中,颠覆性看法就有25处之多。南开大学韩琦教授则通过阅读林恩·V. 福斯特的《探寻玛雅文明》来重新诠释拉丁美洲的玛雅印第安人文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掘工作和地区勘探的深入开展,随着象形文字的高效解读,随着考古学、铭文学、符号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通力合作“攻关”,玛雅文明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许多传统的观点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玛雅文明与中美洲各文明的关系、玛雅文明的政治体制、玛雅人的战争、玛雅文明的经济基础、玛雅文明的社会结构等方面。 与会学者除了考察各自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外,还有学者分析了国外学术界最新的教科书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李世安教授以《20世纪以来的全球简史》为例,讨论了西方较为通用的新的历史教科书。他认为,该教材将20世纪以来的历史分为帝国主义、革命与战争年代、战争与各个帝国的崩溃以及后冷战时代等阶段,坚持了史学传统中的科学精神、求真务实精神与大胆创新精神。李教授还总结了该教材的特点,即全面反映了世界五大洲的历史;加强对21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描述;比较客观公正,对一战的原因与结果、苏东剧变的原因分析等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当然,他也批判了教科书中的某些缺陷,如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反共观点,抹杀世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等。 在介绍和分析国外内世界史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与会学者还进一步讨论了国际世界史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趋势。张顺红研究员提出了学术界需要重视的信息。一方面是“大历史”(big history)的发展。地球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人类的历程如何演进的,都是“大历史”研究的对象。因此,它是一种具有战略眼光的历史观。另一方面是“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出现。他认为,从学术角度讲,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的大战略,尽管当时可能没有这种说法,但应该有这么一种思路。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思考和研究。李剑鸣教授同意张顺洪研究员关于“大历史”和“大战略”的提法。他评论说,从历史哲学角度来说,未来50年,人类历史的发展会走向一个“大历史”的时代。 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则阐释了历史研究中的跨国转向与跨国史的兴起。冷战结束后,国家影响力下降和国家间相互关系渐趋加强,历史学家开始对民族国家史学进行反思。这就导致了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和跨国史的兴起。在他看来,跨国史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视角和方法的跨国史,将民族国家(具体说来是美国)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跨国情境中进行考察。第二个层面是作为研究领域的跨国史,关注跨国(公共)空间发生的跨国事务,强调研究对象的非国家特性,国家被置于较边缘的位置。在他看来,作为研究领域的跨国史约等于国际史。跨国史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它改变、丰富和加深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而不是取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更不是把民族国家从历史研究中剔除出去,而是把民族国家置于更全面和更复杂的历史语境之中;通过突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历史现象、过程和联系,挖掘被忽视和被淹没的历史,在民族国家历史之外创造一种“新历史”;通过对现代历史的重新解释,跨国史研究可以提供了一个新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促进文明(文化)间的对话,塑造共同文化身份,培育国际主义观念和世界公民意识。 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则根据自己完成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知研究”的体会与经验,探讨了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俄国人的中国观等研究的学理性内容,力图建立一种相关研究的认知模式。在他看来,“认知”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主观判断,是解决认识主体眼中的认识客体“是什么”、“为什么”即何以至此的问题。例如,在“是什么”的认知上,要做出客体对象是文明、先进、富裕、强大,还是愚昧、落后、贫穷、弱小的判断。在“为什么”的认知上,要做出是因为思想进取、政治开明、技术发达、社会安定,还是因为思想保守、政治黑暗、技术落后、社会混乱的分析。“态度”则是认识主体基于对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认知而产生的如何应对同一认识客体的主观立场。在这一主观立场中,又包含着认识主体直面认识客体而产生的好恶心态和政策主张的两个层面。例如,在对待客体对象的情感上,认识主体是羡慕、喜欢,还是蔑视、讨厌?在针对客体对象的政策主张上,认识主体是希望接近、亲和,还是疏远、敌视? 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即将在中国济南召开,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史学会所提出议题的情况。这包括大会开幕式的两个主题:文明、人与自然;会议的三大主题:历史的观察——东亚国家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历史、宗教、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会议的20个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战争、革命与和平、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演变与价值、女性与人类、灾害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中的海洋、近现代城市发展进程比较研究、从马背到太空——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毒品传播与毒品史、世界博览会历史研究、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互动、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东西方国际关系——宗藩体制与殖民地体制、东亚文化圈与全球化、宗教研究在历史理解中的意义、传教士与东亚文化、礼仪文化的变迁、考古新发现与历史研究、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北京大学高毅教授呼吁中国学界尤其世界史学科的同仁积极为此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做准备。他认为,这次盛会在中国召开,对于中国历史学尤其是刚刚成为一级学科的世界史来说是一个重要契机,使中国世界史学者能够接触国际史学界研究的前沿,并与国内外学者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因此,他认为中国史学界需要振奋精神,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看看能提出哪些好的课题,把自己的声音打出去。 在关于第二个主题的讨论中,与会学者介绍了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后的学科建设进展,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陈志强教授认为,世界史一级学科建设还是有些准备不足,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人才培养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方面,都需要进过不断的讨论、思考尤其是实践才能逐步完善。高岱教授支持陈志强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如何把世界史一级学科好事做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一定要一级学科的政策优势转变为学科优势。另外,他还力图破除对一级学科认识的误区,呼吁一级学科绝不是一个项目,绝不是给多少科研经费的问题,而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等许多方面都需要用学科的语言来争取,因为学科建设需要是无可回避的,学科的语言是学校领导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对于未来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与会代表都献言献策。杨栋梁教授呼吁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世界史具有重要基础的大学可以考虑联合起来,通过共同研讨来确定一个相对统一的二级学科目录设置,而不是各个学校蜂拥而上,各自为政。张顺洪研究员表示同意,他提议可以设置7-8个二级学科,其中各个二级学科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陈志强教授对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提出了建议:适当扩大《世界历史》的版面,搭建世界史研究的全国性网络平台,定期召开世界史学术研讨会,协调全国世界史研究布局。 张顺洪研究员还探讨了中国世界史学科能否在未来50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问题,对世界史的跨越式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优秀的世界史人才,一是拥有良好的科研条件。人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不断加强。第一个问题是懂多种外语的人才少;第二个方面是能够熟练地运用通用语言英语的人才少;第三个方面是能够运用古代小语种语言如波斯语、印地语、古埃及文等来研究世界史的人少;第四个方面,理论素养好的人才也不多。四个方面的弱点集中于一点,就是研究人才的行政任用,这是制约人才脱颖而出,世界史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当然,目前的科研条件已经很好了。科研人员有充分的科研时间,有较为充裕的科研经费,有较好的科研设备和办公条件,如网络等,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有较为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等。 李剑鸣教授则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跨越式发展持悲观态度。他认为,学科建设的首要因素是提高学术水平。中国学术在大的方向上仍然是在学习西方,未能在大的范式和研究路径上突破西方,也没有能够引领世界学术潮流的方向,因此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另外,中国社会还存在很多不利于学术发展的因素,比如社会腐败因素影响学术发展,许多掌握学术权力和资源的人不能包容多样性,中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令人怀疑。很多学者在稍有名气后就坐享其成,在学术上止步不前。最后,世界史研究有不同的层次,要全面推进也是不可能的。世界史研究有国际性学问如古典学和中世纪学等,中国学者可以加入学术共同体进行讨论。但是如果是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的研究比如英国史、美国史等,要真正达到他们本国的水平非常之难,我们也没有必要和他们争一时之长。李世安教授赞同李剑鸣教授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要走向世界,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在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认可后,才可能与国际学界对话。高岱教授认为,面对世界史学科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我们不应过于悲观,世界史一级学科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都要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丁见民,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